中国历史上的排行制及实名敬避问题(钱杭)
中国历史上的排行制与实名敬避问题
钱 杭
提 要:
中国历史上的排行制是社会人类学界高度关注的重要论题,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广泛深远的意义.其基本功能之一,是以同辈成员间的长幼顺序符号部分地或完全地取代人的实名.由周至唐,随着排行在人名称呼中独立副称意义的逐步增强,排行开始具备实名敬避功能;而宋代在谱类文献中以排行代替正式的名,字,并与专用的数字式辈行字相结合,发展成一种特殊的祖先人名避讳方式.面对严格的尊卑等级制度,对人名进行“数目字管理”,亦不失为一种合理,安全的选择。
一
行辈制,包括排行与辈行两部分,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汉族社会最具特色,且在世界文明史上亦相当罕见的民俗制度之一,具有多层次的意义.以往学者对行辈制的内容,性质多有论述,但对行辈制与中国古代实名敬避制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则较少关注。本文的目的是对排行与实名敬避之间的历史联系作综合考察.辈行问题容另文专论。
“排行”的原意并不复杂,即用序数字(或包含次第意义的专词如伯仲叔季等)来称呼和标志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中同一世辈者出生的先后顺序,文献中也常常略称为"行第","排行顺"(或行次)。排行主要用于日常称呼,时至21世纪,民间社会中依然可见类似习俗. 在日常称呼中使用排行,除了能简便地进行对象定位,另有重要功能,就是增加亲密感,是为"昵称"之一种。家庭,家族之外的人员互称排行所欲达目的,亦为如此.作为昵称使用的排行,所用范围非常广泛,平民,官僚,商人,贵族,皇亲国戚,各阶层各等级无所限制:既可用于称呼下辈卑属亲和同辈幼属亲,如阿大。也可用于称呼同辈及上辈尊属亲,如二哥,十二兄,十七舅。同辈友人之间更为常用,形式是姓加排行,如刘四,张五,柳十二一类。甚至贵为帝王,在唐代也有用排行称呼臣下的实例,如唐玄宗称王琚为"王十一",称姜皎为"姜七",唐德宗对陆贽"常以辈行呼而不名"等等。
排行这种民俗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人类学文献将排行称之为"同一世辈内的年龄之别"(difference of age within one generation).民族志中的相关记载亦很普遍.如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提到反映印尼巴厘岛原住民定位秩序的六大类标签,其中第二类就是所谓"人的定位排行制"(birth order system of person-difinition),格尔兹称其为"最基本的标签":
那些根据胎儿——甚至死胎——出生时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等而自动赋予的标签.这里使用的是一些地方和地位群体的变形,但最普遍的体系是用Wayan指第一个孩子,Njoman指第二个,Made(或Nengah)指第三个,Ktut指第四个,周而复始,用Wayan指第五个,Njoman指第六个,等等. 这些名字本身没有实义(它们不是数词或数词的派生词),甚至不表示真实或可靠的兄弟姐妹的地位或阶层.一位Wayan可能是老五(或者老九!),也可以是老大。
可惜,这种排行制与中国排行制的基本内容和意义相差甚远.有序的定位标签固然可视为排行,但这类会"周而复始",本身又"不是数词或数词的派生词"的标签,却无法成为某人实名之外的一个固定"副称",没有实现当地人希望实现的定位目标,因此实际意义不大. 望从它的背后追寻到伦理的,等级的,政治的等等更深层的含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人们之所以要使用排行——同辈成员间的长幼顺序符号,来部分地或完全地取代人的实名这一前提,却往往在研究过程中被忽略了.事实上,本文所关注的排行与实名敬避的关系,恰恰就基于排行的这一个基点。人类学,民俗学文献曾经广泛报道过存在于世界各地早期历史中以尊敬的目的避称人的本名(即实名),而改称某类代名的现象。
第一,实名敬避与否,关系到对某人家族成员正式资格的认定,和他是否能够参与对家族各项权利义务的继承.如摩尔根所说:"一个氏族成员的名字就赋予它本身以氏族成员的权利";"一个人到了16岁或18岁,通常就由本氏族的一位酋长废掉他原来的名字而代之以第二种名字从此以后,他就要承担成年男子的责任了."
中国古代命名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冠而字之"即具此意.《礼记·冠义》:"冠而字之,成人之道."孔疏:"冠而字之者,此明冠毕加字未冠之前以名别之,既冠之后又改以字,且人二十有为父之道,不可复言其名,故冠而加字之,成人之道也."《白虎通·姓名》:"人所以有字何所以冠德明功,敬成人也."从开始实名敬避的那一刻起,标志着某人将完整地承担起家族正式成员的义务以及享有相应的权利。
第二,对人的实名加以敬避,可能与巫术中的人名禁忌及某种对姓名的原始信仰有关.摩尔根不大重视这一点,他把有些人患一次重病后即要换名的原因归结为"迷信的缘故."弗雷泽则探索了人名禁忌背后的信仰因素.在他看来,对普通人以及国王真名的禁忌,"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也不是宫廷里的卑躬屈膝和阿谀奉迎,而纯粹是原始人思想的一般原则的特殊应用,这种应用的范围包括平民和神,国王和祭司."所谓"原始人思想的一般原则"是:"名字和它们所代表的人或物之间不仅是人的思想概念上的联系,而且是实在的物质的联系,从而巫术容易通过名字,犹如通过头发指甲及人身其他任何部分一样。
换言之,不称某人的实名是为了防止巫术乘机侵害实名的拥有者,从而达到保护某人的目的.中国古代有关实名敬避的正式记载中较少这类系统的说明,但不能说没有.比如在僳僳族,鄂伦春族和高山族的习俗中至今还有部分残余。另据吾友虞万里说,《仪礼·士冠礼》中"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一语,"隐隐地透露出先民对幼年之名的神秘和保护心理,不云'忌畏','忌讳'而用'敬',只是因文明的礼而改换的字面."不过,对这层意义似不应过分强调.按巫术的人名禁忌说,所"敬"者当为"名"本身.而据经师对《仪礼》,《礼记》经文的解释,对某人实名之"敬",实源于对某人实名的命名者——父母之"敬".郑玄注"敬其名也":"名者质,所受于父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也." 胡培翚《仪礼正义》引张尔岐所云:"敬其名,敬其所受于父母之名,非君父之前不以呼也",对名之所应"敬"的原因提示得相当清楚.联系到《白虎通·姓名》所谓"名者幼小卑贱之称"的说法,将人的"幼年之名"作为"敬"的对象未免勉强.而读《礼记·内则》所记子生三月,择日盥洗,父母"咳而名之"的详细过程,由"敬其名","敬其所受于父母之名",到敬避"受于父母之名,非君父之前不以呼也",则是十分合理的结果.因此,实名敬避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体现和维护某种权力的需要。
应该指出,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实名敬避习俗,无论是规则的丰富性,还是实况的复杂性,都无法与中国古代的同类制度相比.中国的实名敬避从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民俗制度发展演变成世界上难得一见的避讳制度。笔者认为,避讳现象的起源和出现必早,但成为系统的社会制度必晚,二者不必统一也无法统一. 历史时期内,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表现形式,其政治意义明显地覆盖了原有的民俗意义,历代学者对这一点已经有清楚的认识.本文所讨论的排行制的真正意义,也曲折地表现在这一过程中。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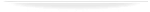
根据目前已知的资料,排行与实名敬避的关系,最早通过为了"敬名"而另取之"字"体现出来;并随着排行在人名称呼中独立副称意义的逐步增强,表现出明显的阶段特征. 在对人名的称呼和命名上(包括日常称呼和文献记载两个途径),周代已经广泛地使用了排行;但此时的排行依附于"字",本身并未取得独立的表现形式,还没有成为准确的人名定位工具.男子二十而冠,冠毕加字,"字"中往往就包含着一个排行.比如《仪礼·士冠礼》"字辞"记录了士以上阶层的"字"所应体现的完整结构:"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当."王力解释"曰伯某甫"云云的意思:
周代贵族男子字的前面加伯,仲,叔,季表示排行,字的后面加"父"或"甫"表示性别,这样构成男子字的全称.例如:伯禽父,仲山甫,仲尼父,叔兴父.有时候省去"父"(甫)字,例如伯禽,仲尼,叔向,季路.有时候省去排行,例如禽父,尼父,羽父.有时候以排行为字,例如管夷吾字仲,范雎字叔,鲁父子友字季,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周代贵族女子字的前面加姓,姓的前面加孟(伯),仲,叔,季表示排行,字的后面加母或女表示性别,这样构成女子字的全称.(例略)所谓"全称",一般用于比较正式的或以文字形式记载的场合,各种"省略"形式则出现于非正式的或以口语表达的场合.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周代的人们特别是平民阶层在实际生活中是否有对排行比较随意的使用,但至少在传世的周殷商先公先王庙号中的甲乙丙丁是否具有排行的意义,学术界一直有争论。
事实上,排行虽不一定仅仅表现为生前的称呼,但至少在数字式"叙谱行"成为惯例以前大致是如此.因此,庙号中的序数词不大可能是排行。古代文献上,排行似乎还没有独立成人名的一个稳定副称,因此就不可能发挥实名敬避的功能手段.与魏晋以后相比,周代的这一显著特点,历代研究者是注意到的,但结论尚不明确。
周代排行制在形式和功能上的有限性,说明当时在一般的社会交往尤其是在家庭和家族生活中,人们尚未充分发现,作为人名和亲属的副称,排行所具有的简便,准确和直观功能,没有感受到在称呼中若使用排行会产生一种特殊亲和力.这很可能与当时家族制度的发展程度和阶段特征有关.晋代以降,文献记载中出现了大量以家庭间即同父兄弟间的"小排行"(又称"本行")为基础的人名昵称(上引阿大,阿三,阿五之类);同时,排行开始与亲族称谓相结合,成为使某一具有广义指向的称谓进一步精确化到个人的补充手段.北齐末年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风操篇》中称:凡与人言,言己世父,以次第称之,不云家者,以尊于父,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已嫁,则以夫氏称之;在室,则以次第称之.言礼称他族,不得云家也.凡亲属名称,皆须粉墨,不可滥也. 父母之世叔父,皆当加其次第以别之.颜之推所言在社会人类学上具有重要意义.亲族称谓的精确化或个体化是中国亲族制度的一大特征,这一特征与实名敬避制互为前提,互为动力.凡在社会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至少在各主要方面)严格遵循等级尊卑制的社会中,亲族称谓必朝特别繁复和精确的方向发展.据许多人类学家的报告,在一些发展程度不大充分的原始人群以及等级制不大严格的社会中,最亲近的亲属间可在周代,排行并非与生俱来,其入名,入字或由称呼加以体现,须受年龄上的限制.《礼记·檀弓上》记载人生各阶段所对应的部分礼制:"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就指出了这一点.这种在不同年龄段实行的不同礼制,在人类学上称之为"人生通过礼仪"(rites of passage)。
可以自由互称实名,那里的亲族称谓系统就较为简单.晋代以后,中国社会等级制度日趋严格,从而导致亲族间不仅不互称名(包括幼名,乳名),连直接称字,称号也被视为非礼,这就使得汉族的亲族称谓制向世界上最繁杂,最准确的一种迅速发展.其主要特征,就是把排行顺(即颜之推所谓"次第")从字,号中分离出来,并与亲族称谓语相结合,使之成为一个在逻辑上和实际生活中没有任何他指可能性的固有名词. 在称谓语中,除了固有名词具有上述唯一性以外,一般的普通名词都具有漠然和通类的性质.摩尔根指出,所谓类别式亲属制(classificatoty)的称谓语体系,"对亲属从不加以说明,而是把他们区分为若干范畴,不论其与自身的亲疏如何;凡属同一范畴的人即以同一亲属称谓统称之", 其表达的亲族关系,就具有复数,多义和统称的性质.在说明式亲属制(descriptive)的称谓语体系中,"对于亲属,或用基本亲属称谓来说明,或将这些基本称谓结合起来加以说明,由此使每一个人与自身的亲属关系都各各不同."而在只表示单一亲族关系的称谓语中,也就是美国人类学家洛伊(Lowie)所阐释的个体式或分别详述式亲属制(individualizing)的称谓语体系中,被称者通常是复数,与普通名词的通类性质相同.以上述三种方式为代表的世界已知主要称谓语体系都不能准确迅速地表达一个最简单的亲属事实,比如"叔".虽然个体式或分别详述式亲属制仅在"父亲之弟"这一单一的亲族关系意义上使用"叔",已经比英语uncle和日语おじさん那种广义的类别式多义性准确得多;但父亲之弟未必只有一人,经常有好几个,仅凭一个广义的"叔"仍难判定究竟要指,可指哪一个"叔".如果按颜之推所言"父母之世叔父,皆当加其次第以别之",将次第比如"五"加于称谓语之上,成了"五叔",就可在已知范围内获得与被称者的固有名词完全同一的唯一性.这样,附加了排行的亲族称谓就能成功克服普通名词的漠然性,实现取代实名的重要功能。
唐代除了在亲族间继续保持称谓的精确化,在一般的社会交往中则通过姓加排行,或姓加排行加官职的方式,作为敬避实名的昵称和尊称.这几类称呼习见于文题,尤其是文人唱和时的诗题.前一类有白居易的《酬王十八李大见招游山》,白居易的《和元九与吕二同宿话旧感赠》等;后一类有韩愈的《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等.王十八,李大,元九,吕二等等(有时再加上丈,郎,兄之类),是将家庭中的小排行直接援用于非亲族人群之中.这类现象的普遍化,。一方面说明人们对实名敬避制相关规则的自觉遵守,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血缘关系的泛化和拟制化的热衷追求.但是,王十八,李大,元九,吕二等一类称呼,毕竟只有在平辈的小圈子内进行直接对话时,或所指对象明确无误的条件下,才能作为人名的副称发挥昵称,尊称功能;一旦脱离特定环境,就成了所指对象不明,甚至连起码的人名指示功能都缺失的一堆符号.《行第录》一类工具书之所以必要,就因为存在着由于排行滥用于亲族之外所造成的混乱状况.
相对于王十八,李大等等,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一类称呼就具备了较清晰的人名定位功能.只要同时担任"补阙","拾遗"者姓王,姓李的数量有限就行.很显然,无论孰先孰后,它们是可以补王十八,李大等等称呼之失的.援引官职而敬称而敬避,是当时的习惯.《礼记·曲礼下》"诸侯不生名"孔颖达疏证:"诸侯南面至尊,名者质贱之称.诸侯相见,只可称爵,不可称名."。孔氏的观点反映了唐代官方对实名敬避制的一般看法.正因为这种制度所具有为了证明这一点,笔者对岑仲勉《唐人行第录》所收191个姓氏中前57个姓氏的人名称呼结构作了粗略的类型区分和数量统计.在全部552个存世人名称呼实例中,姓加排行类为260次,比例为47.1%;姓加排行加官职类为126次,比例为22.8%;姓加排行加名(字)类为128次,比例为23.2%;姓加排行加官职加名类为14次,比例为2.5%;姓加排行加官职加亲属称类为18次,比例为3.3%;姓加官职加排行加亲属称加名类为6次,比例为1.1%.此项统计虽然没有涉及现有全部样本,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却可以大致反映唐代社会的一部分实际情况.至于已故者的人名称呼结构,男子大多为官职加姓加"君",女子大多为夫职加夫人加姓氏。
排行的官方色彩,不免有打官腔之感,作为普遍适用的人名副称故很难为一般人接受并遵循.正因为如此,唐代更常见于文献记载和其他较正式场合的是以下几类尊称: ⑴姓加排行加名(字),如刘十五公舆,王十一起,吕二炅等; ⑵姓加排行加官职加名,如王十将军承俊,王十七侍御抡,何七判官昌浩等; ⑶姓加排行加官职加亲属称,如李十弟侍御,吏部李侍郎十七兄,李处士十二房叔父等; ⑷姓加官职加排行加亲属称加名,如李秘书少监十弟谅之,李大夫七丈勉,李八丈曛判官等. 很显然,以上几类称呼方式在人名指向上具有高度的唯一性;不仅不会在任何场合和范围内造成歧义,在称呼的语感上,排行顺的加入也有效地缩短了官称造成的异姓间的距离感,故成为唐代文人间使用相当频繁的一批称呼类型.但必须注意的是,由于第一,第二,第四类尊称准确得过了头,竟然在称呼中提及了对方实名,因而有违敬避规则.这一现象说明唐代的实名敬避制并不十分严格,尚未覆盖社会交往的各个领域,至少没有被那些率性自由的诗人骚客刻板认真地看待。
三
进入宋代以后,人们一方面继承唐代传统,在日常称呼及文字唱和时继续大量使用姓加排行(或附加郎,兄,丈等)的方式作为昵称和尊称;另一方面,明显减少了在姓,排行,官职,亲属称这样一种综合性的称呼结构中夹称实名的方式.这显然是因为宋代社会父权观念的强度逐渐超过唐代,当然就不会允许存在对实名敬避制随意违反的倾向.宋代在排行的使用上形成了具有一系列重要特征的表现方式.邓子勉《宋人行第考录》所反映的宋代人名称呼情况,充分说明了当时姓加排行方式的普遍性.首先,为了弥补姓加排行一类称呼所指的不确定性,宋代比唐代更频繁地在姓之后加称此人同高祖兄弟间的大排行(又称"通行"),这就使得宋人昵称与尊称中的排行顺数目普遍大于唐代,如方十五,郭十六,许二十四,陈四十,林七十八等等.即使当中有许多大排行数目(特别是二十以后的数字)的精确性颇令人怀疑(详见后文),但至少二十以前的数字基本上可以反映宋代习惯以大排行入人名的真实情况.邓子勉所编《宋人行第考录》为此提供了大量例证,读者可以参看. 不过,这种称呼方式虽然实现了实名敬避,但由于它们普遍实行于同行,同人和中等以下社会阶层的人们之间,因此"昵"的成分超过了"尊".如果将此类称呼直接用之于社会地位上的尊者,则会造成尊卑失序的结果,有悖敬避之本意.当时一些著名文人如洪迈,陆游等,就对此类习俗及相关现象表达了较为明确的批评立场.这说明,一般的实名敬避与封建社会尊卑等级制的根本要求之间还存在着一些重要区别.在许多情况下,昵称固然可以转化为尊称,但从根本上说来,昵称不可能也不允许取代尊称。
宋代在排行的使用上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谱类文献中以排行代替正式的名,字,并与专用辈行字相结合,发展成一种专用的谱类文献。在理论上,辈行具有与排行不同的性质,前者相当于"经",后者相当于"纬",但实际使用上有时区分却不大严格.如顾炎武就把用于命名的辈行字称为排行。
族谱中的用语亦不统一,有辈行,行辈,世派,派行,字派,字伦,字匀(按,"伦"即《礼记·大传》孔疏的伦位,伦列,尊卑伦类,兄弟同伦,世辈伦列等等之"伦".字匀是字伦的转讹音)等等.严格地说,特指辈行,并能与顾炎武等人所说的广义的排行作明确区分的用语,应该是"世派"或"派行".本文为了与"排行"相对应,仍按习惯将之称为"辈行"。
祖先人名避讳方式.随着宗族历史的延长和宗族人口的增加,族谱编撰时迫切需要敬避先人及其他有关尊属,长辈的名字(包括同名,同音字),从而使编撰的难度日益加剧,因此在一般的族谱和联络若干同姓宗族共同编撰的联宗谱,大统宗谱中,就有必要采取简便有效的方法,以避免在纵横两个方向上发生族人重名现象,这就导致了与人名辈行字不同的专用于记录谱牒世系的辈行字的产生和迅速推广.一般情况下,这类辈行字与某人生前的命名和称呼无关,只是为了在族谱上方便地标志出众多族人的世辈区别,所以习惯上将其称为"叙谱行",还有一些族谱称之为"庙行".关于辈行字与避讳的关系,牵扯问题甚多,笔者以后将有专论;这里只简要讨论主要表现在宋代的,某类与排行顺有直接关联的数字式专用辈行字.兹举数例. 例一.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胡荫桐等五修《桐城安定胡氏宗谱》卷首《历世渊源流传系图》,记载五代末至宋初的第51世至第55世: ——义一——承四(讳启南)—智——义二——承一(讳太),承二,承六;祖 ——义四——承三;——义五——承五,承七(生三子,一三公,一四公,一五公)—信——义七——承八;——义九——承九;《系图》中第54世承一实名为"太",承四实名为"启南",说明所谓承一,承二,承三等等都不是实名,"承"不是常见于人名中的辈行字,而是与排行顺相结合,专用以标志世系辈行顺序的一种专用辈行字.义一,义二义九之"义",性质与此相同.出自承七的三公:一三,一四,一五之"一",即为专用的数字式辈行字而非排行顺,两者共同构成了敬避祖先实名的一组专用符号,已经具备了避讳的性质。此例说明,专用的数字式辈行字,是专用辈行字的一个分支.例二.清光绪十四年(1888)岑毓英纂修广西《西林岑氏族谱》,该谱卷1 "庙行"一词来源于祖庙祠堂祭祀中的昭穆序次安排,显然与叙谱行意义相同. 第4册《南阳远祖世表》中,记载了宋代祖先,生于开宝三年(970),卒于皇佑二年(1050)岑孟祥以下四代子孙: 1,同父兄弟2人:二三,讳道,字文载.二四,讳迪,字文吉. 2,同祖兄弟7人:小二,讳山,字汝崖.小三,讳峰,字汝秀.小四,讳岗,字汝高.小五,讳岩,字汝峻.小八,讳嶈,字汝耸.小九,讳崇,自汝宗.小十,讳岸,字汝崖. 3,同曾祖兄弟11人:三一,讳公富,字允吉.三二,讳公适,字允中.三三,讳公逸,字允安.三五,讳公升,字允荐.三六,讳公达,字允相.三七,讳公益,字允谦.三八,讳公孟,字允贤.三九,讳公懋,字允德.三十,讳公惠,字允锡.三十一,讳公贵,字允荣.三十三,讳公远,自允大. 4,同高祖兄弟15人:四一,讳景佺.四二,讳景僖.四三,讳景佑.四四,讳景伯.四五,讳景侞.四六,讳景仰.四八,讳景值.四九,讳景伟.四十,讳景仪.四十一,讳景价.四十二,讳景倍.四十三,讳景侑.四十四,讳景仙.四十五,讳景佾.四十七,讳景侨. 《世表》中的二三,小二,三一,四一等,就是为敬避祖先实名(字)而使用的族内行辈标志组合.同例一,二三之"二",小二 之"小",三一 之"三",四一之"四"不是排行序号,而是区分上下世代顺序的一批专用辈行字;"二三"是指"二"字辈中出生序号为三者;"小二"是指"小"字辈中出生序号为二者(以下义同).再据《世表》所登录的岑景佺(行辈为四一)的后代,其孙子行辈为六一,六二六七;曾孙行辈为千一,千三 千十七;玄孙行辈为万一,万二万十七,万十九.如将"二三","六一","万一"等等认定为排行第二十三,排行第六十一,排行一万零一等,距实情可就差得远了。例三.清乾隆五年(1740)徐天枢等纂辑安徽《休宁徐氏族谱》卷1之徐氏统系,其中的第21世至25世正位于宋代:邓子勉编《宋人行第录》,将宋人习惯所说的"四三哥","五三哥","七五姐"等等,不作具体细致的个案分析,一概认定为排行第四十三,第五十三,第七十五,是在冒极大的风险.从宋代族谱资料来看,"四三","五三"之类称呼在大部分场合下具有特定含义.即使宋人称某人为几十几,也不能贸然将该数字等同于某人的真实排行.一个著名的例子见于《宋史·宗室传》,宋太宗第八子"周恭肃王元俨, 年二十始就封,故宫中称为'二十八太保'.盖元俨于兄弟中行第八也."幸好邓先生只将"虞千一","虞万三"含糊地排在"虞一"之后,没有就此确认此人的排行为第一千零一或一万零三,否则真要离谱了。
《行第录》一类工具书其实并不容易编,资料收集困难固然是一大障碍,望文生义更容易诱编者,读者上当.客观地来说,唐代人较少用"四三","五三"之类称呼,因此在这方面岑著《唐人行第录》就比较令人放心;而使用《宋人行第录》时就要谨慎一些.逢吉(讳兴)—思恭—六(失讳,生三子:念三讳原,念五讳优,念七讳维) —七(失讳) ; —九(失讳) ;辰(讳隆)—思敬—五(失讳,生一子:念九讳升);—八(失讳,生一子:丙十);第24世的五位祖先(排行顺分别为六,七,九,五,八)名,字已被遗忘,后人只知其排行.这一方面说明时代相隔久远致使文献缺漏(这理由其实不够充分,因为此前的第21世,第22世,第23世祖先的名,字就保留得相当完整),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文献记载的场合,排行顺不仅有敬避实名的功能,而且很可能因此就取代了实名,或加快了实名的被遗忘. 就标志宗族世系的传承系列而言,以排行取代实名既不会导致世系的中断,也不会影响子孙后代对祖先的追溯和祭祀.当然,有人会认为失去祖先名讳的记载很不光彩,因而要想尽办法加以弥补,结果反而留下了"伪造"的痕迹.民国十一年(1922)端木彧纂修浙江《东鲁端木氏小宗家谱》卷3《系图·大小宗世系》关于宋,元之际的第52世,第53世祖先是这样记载的: 六七,讳六行七,念四公子. 九四,讳九行四,六七公子. 端木氏以端木赐(子贡)为远祖,世居河南大梁.宋室南渡,随迁金陵乌衣巷及溧水的祖先是47世祖端木倩;明末迁浙江丽水始祖是66世祖端木绅,端木绶兄弟,迁青田始祖是66世祖端木本华.因此,一看第52世祖"讳六行七",第53世祖"讳九行四",就知与端木氏取名惯例不符,不可能是真实记录."六七","九四"是专用的数字式辈行字加排行顺,意思是六之七,九之四.将七,四看作"行"是正确的,而认定六,九为"讳"却不免荒唐.姓加排行固为通例,讳加排行则可决其为必无之事.编者如果如实写下"失讳"二字,断不至于丢人;而为出自孔门高足的祖先生造一个不三不四的"讳",实在是弄巧成拙,有可能被讥为"大不敬".导致编者出此下策的原因,在于他不能让一个至少在观念上保持完整的大宗世系留下空缺,故自认为有责任为大宗"置后".此番苦心当然颇应体谅,然而结果之大谬不然,似不能视为无关宏旨的小事。
例四.1995年聂元芳等编江西上高县《豸溪聂氏六修族谱》卷3"窗下祖居世系",称"豸溪之族实于宋庆历四年祖四十一郎自清碧央田迁居于此,故今豸溪之派特以四十一郎为一世祖云".四十一郎同父兄弟共三人,其中四十二郎分居洋港,四十三郎分居新昌黄海.四十一郎迁豸溪后生子三:十六郎,十七郎,十八郎;十六郎生子一:二十七郎;十七郎生子一:二十四郎;十八郎生子一:二十九郎;二十七郎生子一:四十七郎;二十四郎生子一:四十八郎;二十九郎生子一:四十九郎;四十七郎生子三:千一,千二,百六(原文如此,估计有讹);四十八郎生子一:千四;四十九郎生子三:千三,千五,千六。
据编者聂元芳先生对笔者的介绍,上引聂氏宋代世系传承序列中属于大排行的,估计有四十一郎兄弟,十六郎兄弟等;而二十七郎兄弟,四十七郎兄弟,千一兄弟等,则是以二,四,千为专用辈行字,另外再加同父,同祖,同曾祖,同高祖兄弟间的排行顺.聂先生所说大致不错,基本上反映了宋代关于排行和辈行的观念,以及在世系纪录上以排行,辈行作为先祖名讳的一般做法.明乎此,当我们在族谱中看到宋代一些很特别的人名时就不会感到奇怪.
至于辈行字为何会使用序数字究其原因,可能是受到了排行顺的某些影响,比如,凡在以序数字标志上下两个辈分的场合,辈行高者所用序数字多大于辈行低者;但也不一定.清代学者俞樾在《春在堂随笔》卷5中曾引述徐诚庵对他讲过的一段话.徐氏根据某前辈在《蔡氏家谱》上的一行批语:"元制,庶民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发表以下评论:
此制于《元史》无徵.然证以明高皇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其为元时令甲无疑矣.见在绍兴乡间,颇有以数目字为名者.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或名为五九,五九四十五也。
对此,俞樾深以为然,故进一步补充: 余考明勋臣,开平王常遇春,曾祖四三,祖重五,父六六.东瓯王汤和,曾祖五一,祖六一,父七一,亦以数目字为名.徐诚庵所说,或为辈行字最初使用数目字的原因之一.但从俞樾所举明初勋臣祖先"以数目字为名"的实例来看,这里的四,五,六和五,六,七已不是简单的数目字,而具有了专用的数字式辈行字的性质.总之,以称呼排行为敬避实名之途径在宋,元以后逐渐成为社会的风俗.不仅文人如此,里巷小民也普遍地"言姓第,不言姓名."在谱类文献中,排行不仅是出生先后的序号,而且具备了取代祖先实名进而实现避讳的功能.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一步,不仅因为民俗意义上的便利和直观,还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在中国古人尤其是宋代人看来,面对政治上和社会上严格繁琐,无所不在的尊卑等级制度,准确避讳的难度和成本太高,要修炼至东晋王宏那样"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的火候几无可能.为避免各类麻烦以及由麻烦而引起的灾祸,对人名进行"数目字管理",不失为一种合理,安全的选择.我们从排行与实名敬避,实名敬避与避讳关系的演变中,亦可品味出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股艰涩。